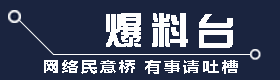●高兴兰
打火石和枞光亮虽同住一个地球上,它俩本来就风马牛不相及,打火石却偏偏遇见枞光亮,就折射出人间烟火与人生的希望。
打火石,原名石火镰,从时间而言,应该是枞光亮的鼻祖。随着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,从青铜器到铁器,从瓷器到钻石,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原始取火的进程,人间才有了烟火。
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,在我的记忆中,当地老百姓把松树叫枞树,是俗名。松树不仅有俗名,而且还是一个大家族。它的种类非常多,除了厚皮枞树、马尾松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外,像黄山松、油松、赤松、白皮松等树种,都是“外来户”或是“移民户”。我记忆深刻的莫过于厚皮枞树。
厚皮枞树的树皮不像马尾松那样细皮嫩肉的,皮薄、光滑,而是弹夹。树皮像壳一样约一公分厚,贴在树的主杆上,呈现千沟万壑的沧桑感,凹凸不平,一块一块的,很粗糙。时间久了,有的枞树根部就会流出一堆白色的颗粒状物质,当地老百姓叫“枞树油”,学名是松脂。这是好东西呀!人们把这些宝贝带回家,放在一个小碟子里,用打火石碰撞出火花后,点燃枞树油当照明用。
还有一种就是枞光亮。枞光亮,学名松明子。据有关资料介绍,它是松树枯死后老化腐蚀,松树的油脂渗透在木质之中,由于长期饱受水蒸气的侵蚀,其油脂聚合部分与木绺丝互相交融,形成浑然一体的物质结构。自然形成的松明子,是深山松树馈赠的稀罕物,一直沿袭到现在。当地老百姓把枯死的枞树砍回做柴禾,取暖煮饭时,干枯的枞树皮燃烧时,就像放鞭炮似的噼噼啪啪发出声响。人们用斧头把枞树砍成一小块一小块当柴禾,偶尔里面有枞光亮,它比一般的木质硬,颜色深红,像瘦腊肉一样。人们把枞光亮划成很薄的小块。它只要遇见打火石的碰撞,就产生人间烟火,山屋点松明,燃起火苗,有了光亮,还散发出一种淡淡的松香味道。为便于使用,人们把枞光亮插在土豆或是一块南瓜上点燃,灯光普照,借着光亮,或煮饭,或读书做作业。
儿时,我就是在这烟火下读书做作业。小火苗像跳舞一样,晃来晃去。待第二天早上洗脸时,我总会从鼻孔里清理出来很多黑灰。那时的我,一心想读书,想用知识改变命运,即使环境再艰苦,淡淡的书香飘过悠悠的岁月,也阅遍艰苦不为苦,只知读书为快活。
随着时代的发展,煤油替代了枞树油和枞光亮,火柴代替了打火石。国家实行计划经济,凭票供应煤油。父亲用一个小瓶,将瓶盖中心钻一个小孔,用一小块薄铁皮卷成一个小管,然后将棉花拧成的芯捻穿管里,瓶里装上煤油,大部分放入瓶内,瓶盖上露出约一寸左右,点上煤油灯,亮度显然比枞光亮的亮度明显增强。后来,市场上有像模像样的煤油灯卖了,圆肚皮、喇叭腿、玻璃罩,随时还可控制灯亮度的大小,每天晚上陪我读书做作业,伴我走过艰苦的年代,用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七十年代初,我就像打火石遇见枞光亮一样,读书真改变了我的命运,点燃了我人生激情的火花,走入教育系统,当起“孩儿王”。那时环境有所改善。我记忆犹新的是,每天晚上老师们集中在一个大办公室备课、批改作业,每人办公桌上亮着一盏马灯,形状滚圆滚圆的,一点线条感也没有,好在灯顶有一个灯盖,四周留有出烟孔,特点是不怕风吹灭。这时的马灯下不再是学生做作业,而是老师在灯下备课批改作业了。无形中一种自豪感涌上心头,我这辈子就注定与学生打交道了,要好好带学生,为国家培养建设者,无论环境多艰苦都要坚持下去。
时代在发展,环境也随着改变,学校添置了一盏充气灯,它留给我印象太深了。充气灯外观一点也不美观,黑不溜秋的,还露出张牙舞爪的样。更逗的是,每次使用前还要打气,就像小时我们玩竹水枪似的。气充足了,用火柴一点,“砰”的一声就着了。我第一次见那阵仗时,还感到挺吓人的。然后将充气灯挂在办公室空中,四周都亮了,把整个夜晚照得如同白昼一般。
到了八十年代初,社会大发展,不仅学校安装了电灯,农村也安装电灯,别说是打火石、枞光亮,就连煤油灯、马灯、充气灯,都已败下阵来,彻底退出历史舞台,让位于电灯,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。可不是吗,打火石是自然的灵光焕发,当它遇见枞光亮,就点燃人间烟火与人生的希望,像一束光引领前行。
人生,走过如歌的岁月,走过平淡的生活,一路走来就像打火石遇见枞光亮,碰撞出人间的烟火,燃起人生的希望。

[打印]
[责任编辑: ]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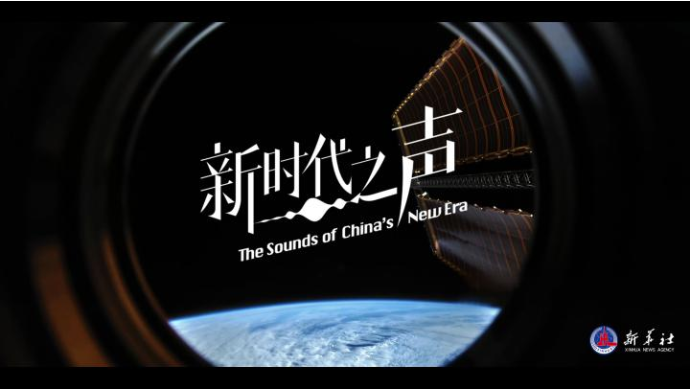
新时代之声
2022-10-1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