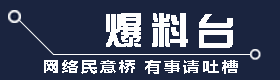●汪万英
教过我的老师们,或谈笑风生,或幽默风趣,或温文尔雅,或循循善诱,或春风化雨。随着时间流逝,他们的身影已渐渐模糊,但总会在不经意间从我尘封的记忆中跳出来,仿佛就在昨天。
冉瑞梅是我小学的数学老师,个子高挑,留着齐耳短发,知性优雅。她对学生有个不成文的奖励,只要专心听讲、积极回答问题,课后就会被邀请到她不大的寝室,听她独奏风琴或者为学生唱歌伴奏。记得那个下大雨的冬天,泥泞的道路使我双脚沾满了泥土,因为课堂上的积极表现,我荣幸地受到邀请,跟着冉老师来到她的寝室外。冉老师开门进屋放下教具,打开风琴盖后,她笑着招手喊我:“小汪同学,快进来呀!”
我激动而羞怯地站在门外,低头望着自己脚上的泥土不敢进屋。冉老师走出来,见我打着赤脚,心疼地说:“哎呀!这个天还打着光脚板,好冷呐!”说完从木桶里舀出两瓢冷水倒入洗脸架上的一个瓷盆,揭开暖水瓶盖倒入开水,兑好了大半盆温水。她把瓷盆端到地上,递给我一把小靠背椅让我坐下将脚放进盆里,蹲下身来帮我洗去脚上的稀泥,再拿毛巾帮我擦干,又取出一双布鞋让我穿上。我冰冷的双脚暖和了,一股暖流涌进心头,幸福的眼泪不自觉地流出来。冉老师摸出手绢替我擦去泪水,拥抱了我一下:“乖,我们来唱歌吧。”说着,她坐到琴前开始弹奏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,我快乐地歌唱,心儿随琴声荡漾。
“假如一个函数f(x)……”上课铃一响,人还在教室门外,洪亮的声音就袭进每个同学的耳朵,我们不由得迅疾安静并抬起头来。循声望去,只见我们的数学老师范少剑把随身的帆布书包往门把手上一挂,一步踏上讲台,把三角板或讲义夹往讲桌上一放,拿上一支粉笔开始上课。他或写方程式或画几何图,从黑板这边讲到那边,时而振臂高呼,时而漫步浅吟,洋洋洒洒,挥洒自如,如将军,似诗人。台下学生凝神屏气,聚精会神,听得津津有味。偶尔见学生注意力不集中,他就讲个笑话或故事,把学生飘远的思绪拉回课堂。
“有个财主好逸恶劳每天拿着书装模作样,年近六十连个秀才都没考上。财主生了三个儿子,分别取名胡子、年龄和学问。一天,财主妻子叫三个儿子上山去砍柴,回来后财主问老婆,儿子们各砍了多少柴?老婆没好气地说:‘胡子(砍)一大把,年龄(砍)五六十(根),学问一点没有(砍)。’”同学们听了哑然失笑,也明白了范老师的良苦用心。
范老师中等个子,留着向后倒的长发,厚厚的镜片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,经常穿一件花格子西装,挂一只帆布书包。他激情满怀、声若洪钟、幽默风趣,学生都喜欢他的课。
我高中的语文老师名叫秦万茂,头发花白,风度翩翩,讲课有条不紊、抑扬顿挫。印象最深的是给我们讲白居易的《卖炭翁》,其中有一句“满面尘灰烟火色,两鬓苍苍十指黑”。他动情地讲:“卖炭翁长期受烟火熏烤,满面灰尘,皮肤变色;终日扒摸木炭,十指占黑儿;两鬓苍苍,表现出他的凄凉和衰老。‘心忧炭贱愿天寒’‘可怜身上衣正单’……”讲着讲着,秦老师眼角沁出了泪花,他被卖炭翁窘迫的生活所感染。当他讲到“夜来城外一尺雪”时,为了缓解沉闷的气氛,他给我们出了一个谜语:“江山一笼统,井上黑窟窿。黄狗身上白,白狗身上肿”,让我们猜谜并分析作者使用的修辞手法。当我们猜出谜底是“雪”、修辞手法是“白描”时,他高兴得手舞足蹈,连说了几个“好”。随后,他又给我们分析了马致远《秋思》中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,古道西风瘦马”的白描手法。从此,白描成了我最欣赏的修辞手法。
“一位老大娘拄着拐杖行走在大街上,她做梦也想不到祸从天降。”老师在讲台上,边讲边模仿,手扶拐杖,勾腰驼背,步履艰难。“一个灰心丧气的青年站在八楼的窗口,他爬上窗台,一跃而下……”他又模仿年轻人跳窗前心灰意冷的表情和跳窗的动作,惟妙惟肖,同学们全神贯注。“结果怎么样?年轻人摔死了吗?”他突然打住问道。同学们议论纷纷,都说八楼那么高肯定摔死了。“NO NO NO!”他连连摆手,看着瞪大眼睛的同学们,娓娓道来:“事实上,年轻人掉下来并没有直接砸在地上,而是砸在那个老大娘身上,把老大娘砸死了,他自己只是受了伤。”他的眼睛嘴巴鼻子神奇地动着,手脚夸张地比划着,引起满堂喝彩。
“你们知道年轻人为什么没死吗?”又引起一阵热烈的讨论。“年轻人从高空坠落,重力势能很大。当他从高空坠落的时候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而且很大,砸到地面的老大娘,把动能传递到她身上将她砸死了。他自己因为受到老大娘的缓冲,延长了作用时间,减小了撞击力,因此只是受伤而没有致命……”这位诙谐幽默、极具表演天赋、被同学们私底下悄悄称为“入错行的表演艺术家”,就是我们的高中物理老师汪喆,那节讲解“动能和势能的转化”的课至今历历在目。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我母校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许多老师都已离岗退休。但老师们的谆谆教诲,却永远铭记在我心中。难忘师恩,感谢老师们的辛勤栽培!

[打印]
[责任编辑: ]

读图 |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重庆怎么做?
2021-07-2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