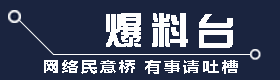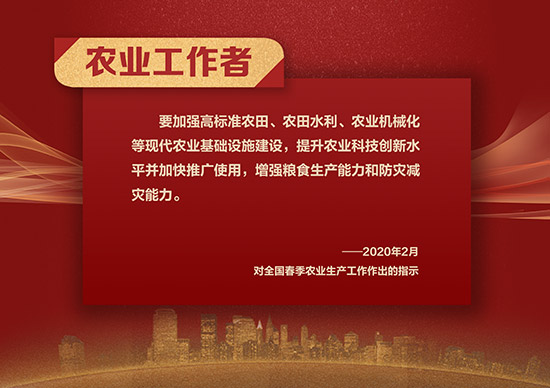●黄玉才
故乡村小是我儿时的母校,现在已空无一人,杂草丛生,那口锈迹斑斑的铁钟,还悬挂在吊脚楼的屋挑上,守望着山里娃的梦想。
我启蒙读书的村小,位于大风堡脚下的斑鸠崖(中益乡建峰村)。村小是典型的土家三合院,吊脚楼坐落在半山腰,四周绿树环抱,流水潺潺,钟声伴随琅琅读书声。
几间吊脚楼改建的校舍,一名教师。一间教室容纳两个年级的学生,以中线为界,一半一年级,一半二年级。读到三年级后,学生们就到离家5公里远的原官田乡场上的官田乡小学就读。
用废旧铁犁铧做成的“时钟”,悬挂在屋挑上,是传令上下课、催促孩子们勤奋学习的号角。每到上下课时间,老师就用铁锤准时敲响铁钟。铛铛铛的钟声清脆悦耳,陪伴老师的青春,学生的童年,寒来暑往,在大山深处久久回荡,也回响在莘莘学子和望子成龙父母的心田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钟表和电铃没有普及,山区小学条件简陋,教室是木格窗子。每到冬季,四周通风,寒风刺骨,几人挤着一张残臂缺腿的木课桌。而那口学生不得随意敲打的铁钟,是师生神圣的“钟表”。
家乡的村小先后迎送了几位老师。第一位是毕业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师范生罗老师,他带着妻子马老师到这里,让学校成了“夫妻小学”,没到一年,罗老师调到原官田乡的白果坝小学任教。学校又请了白果坝一位姓杨的农民任代课老师,刚满一学期,杨老师嫌工资低、离家远,回家开面坊了。第三位老师姓向,是我姨爹,他不辞辛劳,到离家20多公里外的斑鸠崖村小任教。他把家安在村小,外面是教室,内间10平方米左右的吊脚楼走廊是寝室,备课、批改作业、生活起居就在那方小天地里。
向老师当年30余岁,举止温尔文雅。每当上课、下课、放学,他就用铁锤轻轻地敲铁钟,且敲出了动听的旋律。预备钟声是“铛铛、铛铛、铛铛”,连续敲打三下,每次打两锤,上课钟声是连续“铛铛铛、铛铛铛、铛铛铛”地敲打,下课是“铛、铛、铛”地敲打,约定俗成,连在地里干农活的村民都熟悉这钟声。每到放学钟声敲响时,我们要排队唱歌,唱《大刀进行曲》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等歌曲。农人听到放学钟声和学生合唱歌曲,就赶紧收尾庄稼地里的农活,荷锄回家。于是,村庄里家家户户瓦屋上空飘着泥土和饭菜清香的炊烟,山村沉睡在浓浓夜色之中,构成一幅恬静的田园画。
那时的小学是五年制,1972年春天,我离开村小,到官田小学读到小学毕业,学校大殿下的屋挑上,也悬挂着一口铁钟,上下课也用钟声传达。1973年,我考入桥头中学,上下课也是敲打铁钟,敲钟师傅姓傅,人称“老船”,一直聆听他敲的钟声到高中毕业。从小学到高中,我都在铁钟的铛铛声中勤奋学习,书写梦想,憧憬着美好未来。
如今,青山依旧,流水依旧,承载着农家娃梦想的村小的钟声却隐没在了时间的长河里。村庄老去,岁月老去,曾在这里任教的老师也先后去世。那天,我回到故乡,村小那口铁钟还悬挂在屋挑上,锈迹斑斑,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。铁钟已成为浓浓的乡愁,留下一片难以割舍的乡情……

[打印]
[责任编辑: 谢天]

读图 |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重庆怎么做?
2021-07-28